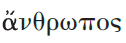图1
一
1890年,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出版了人类学经典著作《金枝》,从学术史上看,这部探讨原始宗教与习俗的著作奠定了弗雷泽作为古典旧人类学家的地位。这里所谓的古典旧人类学自然是与新人类学相对照,那么新旧人类学的区别是什么呢?用人类学家王铭铭的话说,旧人类学家关注人类史的总体面貌,而新人类学则专注于地方性知识,新旧之变的一个突出体现就是人类学与古典学从携手而行到分道扬镳。回到《金枝》,从书名就能知道弗雷泽的古典学旨趣,“金枝”取自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而对于弗雷泽同时代的古典学家来说,弗雷泽另外一项更重要的工作就是他对公元2世纪旅行家波桑尼阿斯《希腊纪行》做的六卷本翻译和注疏。弗雷泽对波桑尼阿斯的兴趣并不奇怪,因为波桑尼阿斯可以被视作投入巨大精力研究古风和古典时期希腊的古代人类学家。
19世纪末到20世纪早期的人类学家中,像弗雷泽这样拥有良好古典学背景的学者并非个例,而是普遍现象。人类学家不仅从古典学中获得启发,而且新兴的人类学对古典学研究也有很大影响。弗雷泽和德国的语文学派直接影响了以英国古典学家简·哈里森为代表的关于古希腊宗教研究的剑桥“神话-仪式”范式;爱尔兰古典学家多兹对希腊人精神世界中非理性因素的研究(《希腊人与非理性》)深受弗雷泽和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等的影响。这一时期,人类学和古典学之间的紧密联系绝不只是学者个人的知识背景或者研究偏好,而是有着更深层的理论预设,这就是对人类社会的演化论式的理解。所有的社会都要经历演化的不同阶段,西方古典文明是人类早期发展阶段的一部分。演化论预设的一个直接结果是用空间解释时间,即通过对当代世界中的某个遥远“他者”的观察,去解释时间上遥远的古代社会。所以就西方古典学来说,西方古代社会就有了双重身份,一是欧洲的过去,二是民族志上的“他者”。
二
古代社会和人类学的关联不只体现在以弗雷泽为代表的原始宗教研究中,在弗雷泽之前的19世纪中叶,出现了一批关注古代亲属制度和社会组织的重要学者和著作,其中最重要的有瑞士人类学家巴霍芬、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英国法律史家亨利·梅因和法国历史学家库朗热等。概而观之,巴霍芬从希罗多德的记述中找到母权社会的线索,提出古代社会中母权是先于父权而产生的,其著作《母权论》一书中也充满了古代神话以及希腊语和拉丁语引文。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则将古希腊、罗马和印第安部落易洛魁人社会制度进行比较,并用对古代希腊罗马文明的认识去解释后者。梅因的《古代法》则以罗马法材料为基础,提出父权家庭是原始社会的基本单位,并且强调了亲缘组织和部落组织、政治组织的区别。库朗热对古希腊罗马社会的研究也是要探讨古代社会的普遍结构,特别强调宗教对于人类社会,特别是法律制度的重要性。
如果回看19世纪中叶的这些研究,现代的学者很容易从他们的著作中找出史实和材料使用方面的问题。随着学术研究的推进,对古代社会的理解必定会不断深化和完善,但人类学与古典学最初联姻所展示出的对人类总体历史的关切,却不能被一并清理进历史的仓库中。真正让人类学和古典学分家的并不是史实的辨析,而是人类社会演化论范式的终结。演化论范式在一战后逐渐被挑战和抛弃,先是古典学界对简·哈里森的剑桥学派提出反思,同时人类学界结构-功能主义范式兴起,对共时性历史解释开始拒斥,而转向对于人文区位地方性民族志的挖掘。无论是人类学还是古典学都开始更关注不同文化自身的语境,19世纪以降的人类学和古典学分道扬镳。
三
人类学和古典学的再次深度互动要到二战以后,以法国古代世界研究的人类学派为代表。该学派的开创者是法国历史学家路易·热尔内,他使用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研究古希腊,并在身后出版《古希腊的人类学》,他的学生让·皮埃尔-韦尔南创立了代表此路径的“巴黎学派”,其他代表性学者还包括皮埃尔·维达尔-纳凯、尼可·洛候、米歇尔·戴地安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该学派不只在法国,而且在大洋彼岸的约翰·布鲁金斯大学、康奈尔大学也“散枝落叶”。巴黎学派结合了结构主义人类学以及英国古代史家摩西·芬利等的研究路径,特别重视从社会组织和民主机制的视角考察宗教、戏剧、神话等现象,极大拓宽了古典学的研究主题。与19世纪古典学界多关注哲学、建筑、文学、修辞学等议题相对,巴黎学派更关心日常生活,并将原来处于社会边缘位置的女性、奴隶、孩子等对象也纳入研究范围,社会群体的习俗和信仰被同等关注。这方面的显著代表就是洛候关于雅典女性的研究,以及美国古典学家弗洛玛·赛特林对戏剧中女性身份所反映的社会和文化机制的研究。
除了开拓新议题,在已有议题的研究推进中,该学派也体现出自身的特色。以韦尔南对《俄狄浦斯王》的研究为例,他在《无恋母情结的“俄狄浦斯”》中明确指出,弗洛伊德用恋母情结的精神分析来解释俄狄浦斯,脱离了希腊社会语境,特别是无视了雅典剧场的社会政治背景。在韦尔南看来,与其说弗洛伊德是在解释俄狄浦斯神话,不如说他自己创造了一个新神话。韦尔南自己对公元前5世纪雅典人心智结构变化的总体阐释线索是“从神话到理性”,在这一过程中“人”诞生了,而剧场则是人诞生的载体。不过,韦尔南认为雅典剧场中萌生的“人”和现代人并不一样,俄狄浦斯等为代表的“人”并不具有现代人的主体性,他们的形象和命运是在彰显新崛起的民主城邦的集体观念。所以,韦尔南和纳凯等在对古希腊神话和悲剧的分析中,并不像列维·施特劳斯那样将注意力全部放在对内容的结构主义分析上,而是更关注悲剧作者的动机以及悲剧反应的社会结构变迁,分析的落脚点都指向城邦。韦尔南将自己的研究方法称为历史心理学,这一新路径带来的研究洞见是古希腊人的“思维方式”必须在其社会结构、宗教仪式与政治形式之中加以理解。在此基础上,不同时代与文明的社会结构和政治宗教形式是不同的,决定了人类经验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文明中也是各异的。这一立场也为比较研究的重启铺平了道路。
戴地安是该学派中对比较研究最为执着的学者,并且从表面上看,他的比较立场甚至有些极端:“比较越多不同的社会越好”,“要比较不可比较者”,等等。与人类学和古典学第一次联姻时的比较研究不同,戴地安的比较有着对古代文明更为明确的立场,那就是将古希腊文明与后世西方人拉开距离。传统上谈及西方文明历程,肯定将古希腊视为来源,古希腊人被认为是与众不同的,作为西方文明后裔,现代欧洲人自然也是希腊文明的后人。希腊的光辉实际上确立了希腊文明的独特性,所以曾被认为是不可比较的。戴地安则是要将希腊文化作为诸多古代文化中的一种,摒弃掉之前的本质主义文化比较的范式,通过实验性的和建构性的比较主义,即通过不同学科的研究问题、视角和知识的交流来互相质疑和学习,从而增进对古代文化的理解。
如果说20世纪70年代以来,古典学中还有努力采用社会人类学理论和视角进行研究的学者,那么目前的西方人类学界似乎已经完全过渡到新人类学研究阶段。现今,人类学已经更多地成为地方性知识的保护者;而古典学近年来也在不断革命,把自己从西方正统降为世界众多文化的一种,朝着自我地方化的方向大步向前。人类学和古典学两个学科似乎又在人类历史高速路上的一个“服务站”偶遇。作为人类学和西方古典学的他者,我们应以更加平稳和开放的心态探究世界上不同的文明形态,将目光更多地聚焦在anthropology的词源anthrōpos(见图1,人)以及人在历史中创造的丰富且多元的文化资源。
(作者:张新刚,系山东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