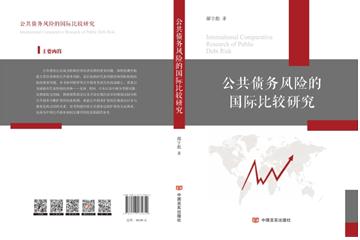
数理模型与实证分析已经成为现代经济学研究的主流范式,在青年学者当中备受青睐和推崇。数学公式和模型是表达经济思想的重要载体和方式,尤其是大数据时代带来的数据革命,更是凸显了定量分析和实证分析的重要意义。然而,如果过度依赖数学工具的使用,却有可能导致经济学问题分析中舍弃一些事实上关键但却无法准确量化的因素。近年来,国内外许多经济学者呼吁应该加强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视角在经济学问题研究中的应用。从方法论来讲,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方法,即思维的逻辑应该反映历史事实发展过程,应该在学术研究中得到充分重视。郝宇彪副教授所著的《公共债务风险的国际比较研究》一书鲜明地体现出这一研究方法的具体应用。
本书首先对世界公共债务发展的历史脉络与未来趋势进行全面和系统的梳理。世界公共债务的发展历史主要经历了五个阶段。二战之前,各国公共债务上升主要是战争的结果。二战之后,伴随着战后繁荣的三十年,各国公共债务负担率总体呈现下降的趋势。然而,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发达经济体的债务风险不断扩大。尽管债务危机得以暂时避免,但许多国家的政府债务压力依然攀升。
为比较分析美国、英国、日本等主要经济体公共债务扩张的原因,本书对这三个国家的公共债务、财政赤字以及财政收支结构的历史变化进行梳理,并分析相互之间的关系。对于美英日等三个发达经济体而言,其公共债务扩张的原因可归结为三个方面:第一,财政支出不断增加。其中,社会保障支出不断攀升导致财政负担不断加大是三个国家共有的特点;军事霸权思维导致国防支出居高不下是美国独有的特点,而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转移支付的负担较重成为英日两国公共债务上升的另一重要原因。第二,从深层次制度层面来看,美英日三个发达经济体财政收支矛盾突出的根源在于西方民主制度与资本主义体系的冲突。第三,从指导一国财政行为的财政预算理念来看,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经历了五次转变。从美国的财政政策实践来看,量入为出的准则对于控制公共债务的增长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从美英日三国政策实践的共同特征来看,新自由主义的财政政策不仅没有消除财政赤字,反而导致公共债务规模不断扩大,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的反危机政策进一步将发达经济体推向债务的泥潭。
与其他经济体情况不同的是,尽管上述三个原因的持续发酵导致美国公共债务不断增加,但美国的负债率却由二战后至1980年间的下降趋势转变为1980年以后不断上升的态势。美国负债率逆转这一有趣事实的发现同样得益于“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思考方法。本书认为,美国负债率逆转的原因有以下三点:第一,1980年以后,GDP的增速除了在克林顿执政期间稳定外,整体呈现逐渐减缓的态势。进一步对经济增长 “三驾马车”的分析发现,GDP增速趋缓主要是投资率的不断下降和对外贸易逆差不断扩大所致。第二,财政收支失衡加剧。在财政支出方面,由于美国失业率居高不下、贫困率不断上升、老龄化程度不断加剧,导致美国社会保障支出不断扩大;在财政收入方面,在收入分配恶化和减税政策的共同作用下,美国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不断下降。第三,财政收支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二战至1980年间,尽管财政收支有所失衡,但财政支出与收入结构均有利于经济增长;20世纪80年代以来,财政收支失衡进一步加剧,但财政支出与收入结构的变化总体不利于经济增长。
公共债务的不断增加会从各个角度对经济发展造成影响。遵循历史与逻辑一致的原则,本书从经济思想史发展历程角度,分别对古典主义、凯恩斯主义以及当前经济学界对公共债务的宏观经济效应的观点进行梳理。在理论梳理的基础上,以1980-2014年104个国家的数据为分析样本,实证检验了公共债务扩张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整体样本的检验结果显示,负债率的上升不利于实际经济增长,且这种效应长期存在。从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分类型检验的效果来看,发达经济体负债率上升对实际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在统计学意义上不显著。但相比较发达经济体,新兴经济体的负债率上升对实际经济增长的负面效应较突出。本书作者认为,其可能的解释为新兴经济体的财政制度相对松散,现代公共财政制度不够完善,黄金财政规则得不到贯彻落实。
除上述分析之外,本书还探讨两个比价有意思的延伸性问题:一是社会保障制度与失业之间的关系;二是公共债务规模与债务危机之间的关系。对延伸问题的讨论也同样体现这一原则。
针对学术界争论的社会保障制度与失业率上升之间的关系,在理论辨析的基础上,本书以OECD35个成员国1980—2015 年的数据为考察样本,对社会保障制度的失业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20 世纪80 年代社会保障支出增加会加剧失业;但随着1990 年以来的社会保障制度“再商品化”改革,社会保障制度的“道德风险”有所减弱。当前社会保障支出不再加剧失业,但失业是社会保障支出不断高企进而导致政府公共债务风险扩大的原因。
关于公共债务规模与债务危机之间的关系,本书认为,公共债务规模扩张至何种程度会导致债务危机,各国的债务临界值不同。究竟债务负担率达到多少就会引发债务风险,这与各国的政治制度、经济状况、财政状况、债务结构以及金融发展相关。一国是否会发生公共债务危机,关键的因素在于债务的标价货币是否主权货币。如果是主权货币标价,那么就可以通过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相协调“隐性违约”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化解公共债务风险。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本书最后提出约束公共债务扩张的方法——构建新财政预算理念。构建的新财政预算理念框架如下:其一,财政总量规则采取“动态预算平衡+债务规则”的规则组合;其二,财政支出遵循以下原则:财政总量支出需遵守黄金财政规则;政府的投资性支出须符合公共财政导向性原则;对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结构比例建立数量限制规则。其三,税收制度必须立足于促进资源有效配置和调节收入分配。其四,从制度保障和机构保障两方面构建新财政预算理念的实施保障机制。对比上述原则,针对我国公共债务风险防控,本书提出四条政策建议:一是推动经济治理现代化,建立科学的宏观调控体系;二是明确财政政策首要目标,强化公共财政型财政体系;三是坚决破除唯GDP论,改革完善官员考核体系;四是完善地方政府信用评级体系,推进地方政府债券市场发展。
(作者系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国际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