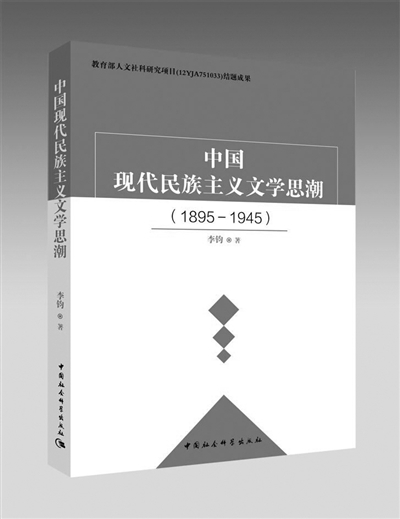
《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1895—1945)》 李钧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4月
《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1895—1945)》是李钧教授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结题成果,全书50余万言,主体上中下三编,既有宏观的思潮脉络梳理又有微观的个案深度剖析,不仅论证了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更以辜鸿铭、刘鹗、陈天华、黄震遐、老舍、萧红、林语堂、鹿桥、吴浊流等人为代表,阐释了民族主义文学的时代性与艺术性,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研究的拓深力作。
《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1895—1945)》研究意图明确,逻辑理路清晰。专著以1895年中日签署《马关条约》、清政府被迫割让台湾为起点,以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为终点,构成了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思潮研究的一个自洽的历史单元;复以曾国藩、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为代表,梳理了中国近现代民族主义思想的发生原因与嬗变;随后以丰赡的文学史实论证现代民族主义文学的合理性,以经典作家作品为个案阐释民族主义文学的艺术性,从而形成了一个合理自足的逻辑体系。著者认为:中国现代民族主义超越了“天下观念”和“大汉族主义”,是建立在“中华民族”历史共同体基础上的“国族主义”,可以说是“中国梦”的最初显现;虽然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的题旨异常丰富,但主体可分为政治民族主义文学与文化民族主义文学两大类;政治民族主义文学“正面阐释‘国家至上’‘一切以国家为重’的民族国家观念,书写政治、外交、军事、战争等宏大主题,是对国家独立富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想象与表达”;而文化民族主义文学则表现中国民族的“优根性”和文化自觉,形成了“文化中国”与“大地民间”母题,以期“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在民族危亡之际得以创造性转化,以激发国人的民族认同感和文化自信心”。对“关键词”的“知识考古”式的厘清以及条畅不紊的论述,显示出著者卓越清晰的逻辑理路与雄辩深刻的思辨能力。
《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1895—1945)》尝试方法论实验,力图以“生态文化学”破解文学史书写的范式困境。李钧教授明确反对以论带史、以论代史的唯理主义先验论,认为宜以“生态文化学”为文学史观,将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安置在宏阔开放的历史视野之中,探究民族主义文学与启蒙主义文学、革命—左翼文学之间的互动互渗,这样才能冲破固有的文学史书写范式困境,从而呈现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内涵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历史的合力”形成了丰富多彩、复杂多元的文学样态与文学生态,同一历史时期内共存的文学思潮之间并非绝对泾渭分明,往往有内在的联系与隐秘的竞争,因此必须从具备全局性、整体性与系统性特质的“生态文化学”角度审读评判研究对象,才能解决“一叶障目不见森林”的局限性和视野狭窄造成的弊端。《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1895—1945)》也证明了“生态文化学”能为文学史书写提供疑旧立新的方法论。比如著者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对黄震遐等人的作品进行了重评,指出《黄人之血》是“中东路事件”背景下的“浪漫主义诗剧创作的尝试”,而《大上海的毁灭》则是“淞沪会战”背景下的“一个人的抗战”;再如著作认为“战国策派”主张复兴中华民族“大夫士”和“国家至上”的刚道文明,在抗战背景下既主张新权威主义又明确反对纳粹主义,从而突破了过去的文学史简单粗暴地将“战国策派”视为拉历史倒车的“反动社团”之成见。“生态文化学”方法论以及著者大胆质疑的精神与锐意创新意识,使得专著洞见迭现,对于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研究深具拓深之功。
《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1895—1945)》对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进行了深入勘探、多维考辨,形成了学术研究的“火力交叉点”。文学史研究主体需要具备史家之博富、诗家之激情、论者之理性,注意将研究对象放置于历史的、思辨的与审美的三个维度中进行考辨评判;如果只强调其中一维,则往往得到片面的深刻。诚如著名文学史家朱德发先生所说:“史家灵魂要获得一种圆融独到的‘文学史理念’或‘史识’,必须借助于主体思维的超越性和创造性、适应性与整合性,因为它不是从先验的理念出发将研究对象‘削足适履’,也不是以二元对立思维将研究对象拆得支离破碎,而是以完整体悟与通达理解的姿态去感受、发现对象灵魂,使得研究主体的灵魂与对象主体的灵魂相对应,相契合。”(朱德发:《现代文学史书写的理论探索》,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54页)
《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1895—1945)》坚持让海量的史实说话,以文学史信息为证,绝不发无稽之言、立虚妄之论;大到民族主义文学社团与文学刊物的史实,中到人物小传,小到每部作品的内容细节,著者均力求翔实准确,充分显示了严谨扎实的治学精神,做到了言之有据而不被海量的文学史料所掩蔽,言之成理且始终追求“重回现场的历史感”,既努力进行审美的评判又避免陷入“为艺术而艺术”的狭促视野;从专著主体部分的上中下各编论述来看,著者的论断不仅由扎实的史料、高度的思辨与艺术的审美中归纳概括提炼而成,而且达到了“研究主体的灵魂与对象主体的灵魂相对应、相契合”的高度。著者也深知,文学史书写与一般历史研究不同,需要呈现文学家生命的质感与文学创作的美感,因而在专著中编和下编对中国现代民族主义作家作品进行了精深论述,既显示出著者超群逸伦的审美感悟力与精准的文字表现功力,也很好地实现了著者“以诗证史”的初衷。
(杨新刚,文学博士,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