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为对象的规律的研究与对法律文本意义的解读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良好的法律制度必须建立在对人类决策与行为的深入研究基础之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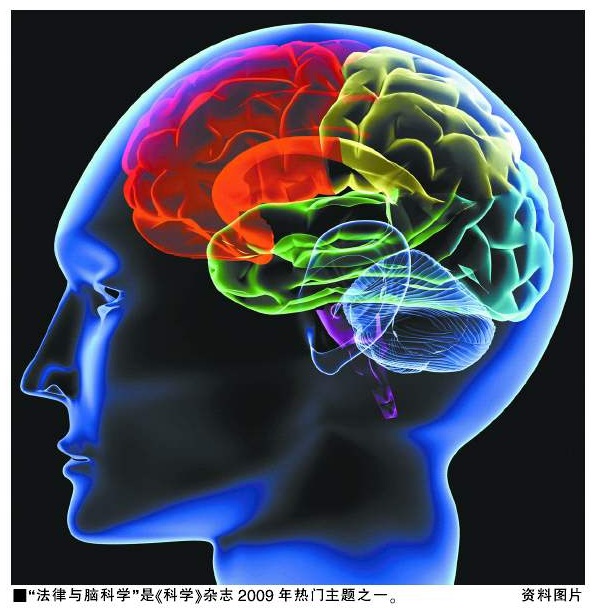
19世纪,以特定国家实在法秩序为研究对象的法教义学逐渐成为法学的主流。法教义学将法律文本当做神圣、权威的文本进行解释,解释其中的“意义”。
法教义学意义上的法学是一门人文学科
法教义学的这种思路使法学很自然会被划归人文学科,不仅区别于自然科学,也区别于借鉴自然科学思考模式的社会科学。从马克斯·韦伯“人是意义的制造者和沟通者”的观点看,法律这一权威文本,正是立法者用以传达意义的载体,立法者希望这种意义载体能够影响每个社会成员的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讲,法教义学及其类似的法学研究,具有非常典型的人文学科色彩。
自然科学则试图揭示世界普遍的运行规律,弄清楚一个现象和另一个现象之间的相关和因果性,并运用这些关于物的知识来改造自然。自然科学并不涉及“意义”,因此在传统法学者看来,如果非要谈论法律与科学的关系,科学无非在证据的发现和对案件事实的还原、揭示方面发挥一定的作用。
主流法学对“价值无涉”的批判
以法教义学为代表的法学理论,对科学主义提出了严厉的批判。但比较有力的批判主要集中在科学主义追求价值无涉,而法学是以价值问题为导向、解说规范性问题的学科,自然科学无法回答“价值”取舍、选择的问题。
对科学主义的批判,其智识源头主要来自休谟对事实与规范的两分。基于事实与规范的二分法,传统法学家指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式的经验研究方式仅仅处理“是”的问题,无法为“应当”提供一个合理的说明;而法学研究总是关于“应当”的问题:面对某个具体案件,法院根据已有的法律应当如何判决?针对新的问题,立法应当如何规定?
跨学科研究的兴起弥补法教义学的不足
法教义学的主要问题在于:法律文本是用来影响人们的行为的,对法律意义的解读必须同时伴随着对人们行为模式、决策过程的深刻了解。但以文本为中心的传统法律研究方式没法告诉我们人类个体是如何行为与决策的。人们不得不向其他学科寻求更有说服力的研究方法。
近年来,无论是在整体意义上的人文学科,还是在法学界内部,都兴起了跨学科研究。在法律领域,最近十几年,国际学术界的跨学科研究并非局限于在社会科学与法学之间做某种跨学科研究(如传统的法律社会学、法律经济学),而是在自然科学与法学之间实现“大跨步”,比如脑科学与法律、神经生物学与法律、进化论法学等。甚至有脑科学实验室中的科学家,在一篇名为《神经科学彻底革新法律》的论文中,大胆地宣称神经生物学将“彻底变革法律”。尽管上述说法略显夸张,但自然科学界对法律的重视却可见一斑。《科学》杂志2009年的七大热门主题之一就是“法律与脑科学”,可见其影响之大。在传统的人文社会科学这一边,法学家也开始有意识地运用认知科学、行为科学的方法来研究法律规制的相关主题:负责奥巴马政府白宫办公室信息和管理事务的孙斯坦(Cass Sunstein)教授,在法律规制领域使用了大量自然科学,尤其是认知科学的方法;而英国首相卡梅伦上台后,内阁办公室成立了行为研究小组,由行为心理学家组成,主要负责行为学方面的研究并对政策制定提供意见,取得了良好的社会与政治效果。
寻求一种更加开放的法学立场
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打破学科藩篱的研究方法并不是最近几十年间学者的创新。亚里士多德首次提出了现代科学、人文体系中的学科之别,把人类的知识分为伦理学、生物学、物理学和形而上学等。但同时,亚里士多德并不将这种学科的界分看做是研究的藩篱,相反,他的伦理学、生物学、物理学和形而上学共享着同一套解释方法,目的论的世界观贯彻着他百科全书式的作品。最值得注意的是他的伦理学,实际上,他认为伦理学是生物学的延续,对于“正义”、“美德”这些主题的探讨必须建立在对人类这种生物根本生活方式的理解上。从这样的视角看,对法律文本意义的解读也必须建立在我们对人类作为一个生物种群的科学研究的基础之上。
换言之,以人为对象的规律的研究与对法律文本意义的解读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良好的法律制度必须建立在对人类决策与行为的深入研究基础之上。人文科学所关注的“意义”总是和一定的自然过程的规律联系在一起,比如同情心与“镜像神经元”的机制、正义感与催产素、对权威的服从与5-羟色胺,对人类意义的认知科学探讨可以让法学家更清楚外在社会环境、物质条件、个体生理因素与法律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设定更好的立法目标、更有效地执行法律、取得最佳的法律效果。孙斯坦所从事的正是这种意义上的工作。无独有偶,当代的法理学家布莱恩·莱特(Brian Leiter)也强调自然科学在法律基础理论研究中的基础性地位,甚至提出“自然化法理学”,与亚里士多德的看法不谋而合。
从法学教育的角度看,当今世界的一流法学院,其崛起主要依赖于两种途径,一是依赖法学教育的组织形式、教学方法的创新,比如哈佛大学在19世纪末创设了现代法学院(Law School)的新教育组织形式,最终使之成为世界法学研究的中心;二是与某种新兴的、有希望的法学流派、研究方法一起成长,比如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院的发达,就分别与法律现实主义、法经济学以及“法律与社会”运动等理论的兴起有着直接的关联。
在最近十年,国内传统理工科为主导的大学,都纷纷开办法学院。上述对法律与科学的看法,可能为传统理工科大学法学学科的发展提供一种全新的思路。如果说传统的人文社科性大学的强项在于对法律文本意义的研究,那么那些以自然科学见长的大学的优势在于——借助科学、法学整合的跨学科研究方式,在尊重法教义学在职业教育中的主流地位的同时,可能可以实现侧翼超越,在短时间内令中国法学研究实质性地达到引领世界法学研究潮流的目标。而这需要中国法学界对这种跨学科的研究抱有一种更加开放的学术态度。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厦门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