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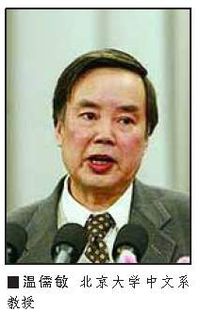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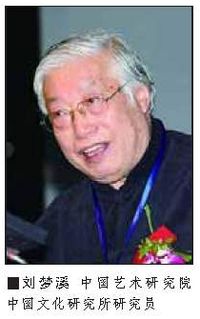
如今,在人文学术的广泛层面上,中国学者对世界各地中国文化研究成果的接受、理解、把握和回应已经有了一个学科化倾向。为了推进这个学科的发展,有几个层面的问题是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首先是关于在汉语文化语境中对该研究对象的核心内涵怎样定名的问题。有的学者把它称为“中国学”,有的称之为 “汉学”,有的称之为“中国研究”等,我认为,汉学的名称很典雅,但与研究对象内涵和价值本质不太一致。研究对象需要正名,这关系到对研究对象的理解、把握和阐释。
孔子在他一生的活动中首先注重的是正名,“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一般说来,“汉学”这个概念起源于乾嘉学派,它以儒学经典的考据与阐释为核心,用来与宋明性理之学相应。18世纪中后期之前的欧洲、19世纪中期之前的日本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人们称之为“汉学”,由于其研究内核具有相应的“应接关系”,所以我以为是合理的。
随着欧亚近代化的发展,由于大航海与探险活动的推进、殖民主义的发展以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自身的提升(例如考古学、民族学、民俗学、人类学等的拓展),欧洲18世纪后期以来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日本19世纪中期以来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在内涵的价值层面与外在的研究材料层面便有了重大的变迁和改观,面对这一学术内核的根本性增量和价值观念的移位,我以为采用“中国学”的概念是比较合理的。
我们要充分认识到中华民族的文化是多元性的文化,充分认识这一多元性的历史价值的现实性与意识形态意义,以及对未来人类文明所能作出的贡献。如果我们在21世纪仍然把世界对中国文化的研究称之为“汉学”就不大合理了。我希望在命名的时候要根据研究对象内涵的不断变化与时俱进。
中国学界一般把国际对中国文化的研究视为中国文化研究在世界的延伸,这当然是对的。但如果仅仅是这样的认知,则又是很表层的了。我认为各国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实际上是具有它本国的思想文化乃至意识形态的哲学本质,也就是说,这个研究首先是对象国文化的组成部分。我个人认为,研究者无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研究者内具的哲学本质是属于他们本民族、本国文化的。日本中国学是日本文化的组成部分,美国中国学就其本质来说是美国文化的一个层面,可以这样依次类推。
重视这个学科的本质有什么意义呢?当研究进入研究对象具体文本的时候,我们应该首先把握的是对象国文化意识在特定时空的基本层面上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厘清各国中国学的学术本质,把握这些学者无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智慧的价值,并进而理解中国文化在参与世界文明进程中的真正价值,同时还可以警惕我们自我学术中心的观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不太赞成把国际中国学仅仅看成国学的自然延伸,它是一门“跨文化”的具有自我哲学本质的实证性学科,其具有的哲理性观念只有在理解对象国的总体哲学思维中才能把握和确认。
当我们在把握对象国对中国文化研究的时候,应该充分地意识到在以个体形态表现出来的研究中常常具有世界性的因素。也就是说,随着世界文化的发展和互相融通,每一个特定国家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和每一个学者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是与“世界的研究”联系在一起的。我们要非常小心地发掘他们自身内涵的“他者”,这些“他者”的文化因素常常呈现为他们的话语力量。比如说德国普鲁士专制主义的理念,对20世纪日本的儒学研究有过潜在的意义。20世纪20年代日本中国学提出的“中国文化中心移动理论”,对美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发展起来的“中国区域文化研究”观念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在中国学研究中,研究者还应该非常重视研究的文本问题,特别是要重视文本的原典性问题。无论是国别研究,还是个案研究,从本质上说,都是在接受中国文化的学术氛围中形成的。追根溯源,探讨他们学术形成的过程,应该十分重视他们接触过的相关文本,研究这些文化的传递及所呈现的多种文化形态。要重视和把握研究文本的各种问题,首先要非常重视我国文化典籍在世界各个国家、各个层面流动的轨迹和形态。在文明史的总体进程中,中国文献典籍在世界的流动表现为多种传播形式。它的影响有时候超越了研究者的想象,所以我们当前最迫切的是需要尽力厘清中国文献典籍在世界各国流布的事实与轨迹,以及对他们的文化产生的影响和后果。
我们现在不必急于在全世界收购中国文献,应认真、踏实地在世界各地阅读中国文化典籍,并且把不是被他们用掠夺手段取得的文献典籍留存在那里,使对象国的中国学家世世代代有阅读和研究的原典。我们需要考察的是典籍在异国流动的轨迹,知道它们对所在国文化继承造成的影响,从而以典籍为基础,可以在学术的图谱上把握中国文化对世界文明发展的贡献。我希望在这个层面上,国际中国文化的研究者与图书馆学家联合起来,以跨文化的国际视野推进这一基础性的学术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