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文学”概念出的最早提,是在1985年前后。其时,《当代文艺思潮》发表了一组文章,针对文坛创作实际,特别是有关西部作家的创作(主要还是指西北作家)进行专门讨论,使“西部文学”的命名正式现于文坛。然而,由于《当代文艺思潮》的停刊及批评界的漠视,西部文学在新时期初的文学格局中,既没有形成大的气候,也没有在评论界和学界取得公认的地位。一个新的话语空间虽已打开,但旋即被缩水,这种状况直到90年代才有所好转。
文学史叙述中的遮蔽与失真

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决策的提出及实施,“西部文学”也以浩大的声势在文学创作及研究领域再次崛起。但不难省察,90 年代以来的这种西部文学研究“繁荣”的背后,更多的是“非文学”性质的因素在起着作用。也就是说,在国家行为及其“舆论导向”的运作下,许多研究者才将目光投向西部文学,如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及西部各省区所设置的“西部研究”课题的有力倾斜(文学研究当然不在例外),都促使西部文学研究逐渐被纳入到主流话语的轨道中来。但因为这次西部文学热的产生主要是基于舆论导向的运作,而不同于80年代初是从其自身发展态势中孕育的学术自觉,所以,在学界并没有出现预期的提升,而文学史中的西部作家仍被史家有意无意地遮蔽。
反思这种轻慢和歧视,对研究者而言是必要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更清晰地透视西部文学的现实存在,并拓展其生存空间。西部文学概念的提出,本身就意味深长。从那个时候起,西部文学在某种意义上只是被当成了“寻根文学”的一部分,在当代文学史叙事中,张承志、贾平凹等西部作家的声音常常被淹没在“寻根文学”的浪潮之中。
将西部作家进行分类并设法归入各种“思潮”,是当代文学史叙事的一个策略。我们在目前较为通行的当代文学史中(90年代以来以“当代文学”命名的著作已不下几十种),实在找不到“西部文学”这个说法。如果我们稍作延伸,仅以当代文学史而论,对地域文学现象的理论升华就有不少,如“山药蛋派”、“荷花淀派”等,史家对之也是乐此不疲。这样,令人费解的问题便产生了,是西部文学真的没有实绩形成所谓的“派”,还是叙述者故意对西部文学现象视而不见?毋庸置疑的是,西部作家自八九十年代以来的创作,其文学贡献并不在“山药蛋派”或“荷花淀派”之下,而且研究者对西部文学多年的探寻已足以上升到理论高度,但“西部文学”之说在史著中仍为一片空白,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注意。并不是说文学史不应该以思潮的演进作为主要线索进行书写,但以思潮的演进为不易之法来应对丰富多彩的文学现象,显然会生捉襟见肘之弊,并造成这样那样的遮蔽与失真。西部文学的遭遇即其一例。
反思西部文学研究
除了追问文学史叙事中可能或已经出现的遮蔽与失真外,对西部文学研究本身的反思也至关重要。事实上,“西部文学”作为一个研究领域,还存有较大的商榷空间,更由于国家行为、历史遗留等因素的介入,许多关键性环节其实是众说纷纭,尚未形成统一的认知。纵览近30年来的研究,首先碰到的一个问题便是,究竟什么是“西部文学”,它是指一种区域文学、地域文学,还是地理概念上的文学?和这一问题相关联的,是它究竟属于西部作家创作的文学,还是在文学中反映了“西部的东西”的都可看做是“西部文学”?尽管研究者不时对这样的问题有所探讨,仍难见到有足够说服力的界说观点。这也就成为制约西部文学研究向纵深发展的瓶颈。
说到底,“西部文学”无非只是一种文学形态,虽然这个概念包含着一个容易引起争议的方位词“西部”,却并不意味着文学可以分为东部、中部或者西部。简单地从地理方位与行政区划,或者政治与经济的意义上来界说“西部”,并进而界说西部文学、西部作家则无异于隔靴搔痒、缘木求鱼。另外还有一点也常常被研究者所忽略,即“西部文学”概念的提出,是以大量的文学事实为前提的,在80年代的研究者那里,就特别注意从文学实践出发讨论何谓西部文学。当然,“西部文学”的创作实践与“西部”天然地有着内在联系,而这种联系主要表现为“书写西部”,将“西部”文学化。文学西部虽然与地理西部的真实性有关联,但已被赋予超越空间真实性的更多的意义,使其具有了更多如审美的、想象的、虚构的能指。而这些能指也许是研究者更应该关注的元素,因为这些元素对定义西部文学更为重要。[page]
文学赋予“西部”别样的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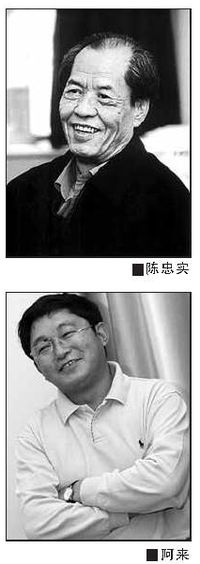
那么,“西部”在西部文学中又是怎样被文学化的?西部的哪些东西被不断地文学化?传统意义上的西部又是如何进入文学视野的?作为文学化的书写对象,“西部”必有其特殊性,这些特殊性实际也表现在文学的各个层面,正是由于这些特殊性才塑造了西部文学的独特形象,并使“西部文学”概念借此获得了合理性。
西部文学中“西部”的自然山川、气候时令、人文地理有其特异的色调,如崇山峻岭、戈壁沙漠、草原牧场,如胡杨、沙柳、骆驼刺,如苍鹰在静寂的天空盘旋滑翔、骆驼在烈日下迈着艰难的步履跋涉、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文学叙事中的“西部”,是一个多民族话语的展演空间,是一个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混杂的地带,是一个汉唐文化、陇右文化、敦煌文化、草原文化、雪域文化、大漠文化、绿洲文化寄生的土壤,是一个伊斯兰教文化、佛教文化、道教文化、基督教文化等宗教文化融汇的场域,因之,西部文学的叙事话语便有了其特殊性,即它总要或隐或显地呈现这样那样的地域文化元素。
沉厚的历史积淀与多元文明的深度撞击,使“西部”在凝重之外难免有一种悲慨的沧桑感,这也使西部作家总是能够融入社会的边缘及其底层去捕捉形形色色的人物,于是便形成了西部文学中人物谱系的特殊性。仅以甘肃作家为例,就有王守义创作的流浪汉系列、淘金者系列,张锐创作的盗马贼系列,邵振国创作的麦客系列等。恶劣的生存环境、悠远的历史传承、丰富的文化样式以及相对封存的人文生态,都在无形中规范着西部人的性格,由此也形成了“西部人”性格的独特性。
西部人为了生存和繁衍,向着多舛的命运进行了多少惊心动魄的抵抗,他们对于人生对于世界所产生的忧患感,远比富庶之地的人要沉重复杂得多,但多舛的命运同时唤起的是西部人对于自身价值的自觉与自信。更由于历史传承与文化塑型,使西部人的历史文化性格还表现为多种相反相成的结构,这才是西部人精神存在的文学表达。
由此不难看出,西部文学中的“西部”尽管与地理方位、行政区划,或者政治、经济策略有一定的关联,但其根本在于,是“文学” 赋予了“西部”以别样的意义,也只有在文学的视阈中,“西部”才显得如此的多姿多彩与耐人寻味。
建构“西部文学”大视野
如果说所谓西部文学即是从大量“写西部”的文学经验中提升的一种文学形态的命名,那么这种命名更多地是出于“研究”的需要,而不是因为西部作家的表白。事实上,我们至今还极少发现哪位西部作家公开承认自己就是西部作家,只不过研究者往往将他们作为西部文学的创作主力来研究罢了。
从学术研究的层面看,这种对于“西部作家”的指认,其实既成就了他们同时也局限了他们。所谓“成就”,是把他们放在地域文化环境中加以发掘,能够更好地把捉他们的创作特色,揭示其创作的优势及本土资源;所谓“局限”,是指由于过分凸显他们创作的地域性因素,往往又忽略了他们创作中生发出来的(或者说走出地域的)文学所具有的普遍性的人性、人道以及“人类性”的诸种内涵,使对其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受到限制。
如果过于强调“西部化的文学” 或“文学化的西部”,显然使其在总体上容易产生几个误区:一是可能沉迷于渲染西部陋习及暴力色情的“想象化”描写;二是可能使题材选择、主题开掘、风格表述诸方面趋于单一与单薄;三是可能拘泥于具体的政治战略的图解,甚至政策化的形象叙事。因此,无论是创作还是研究,西部文学都应该在立足本土、面向全国与世界、放眼未来中去促进与外界的密切交流与健康成长,从而重铸自身的文学史形象与价值。而要真正回归文学,关键还在于作家——作家的素养、作家的视野、作家的胸襟、作家的人文关怀等等,这才是西部文学走出“西部”、超越时空的关键。
因此,应该建构一种“西部文学”的大视野,这种视野是开放的而不是闭锁的,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它不仅是指西部本土作家的“身份”指认,也不仅是指作家叙说了西部的自然景观、世态人情、生活境遇以及言说西部历史的、现当代的、未来的并能够体现西部多民族的生存相、生态相、情绪相、精神相的文学,而更重要的还在于这样的文学是能够源于地域又能够超越地域限阈的文学,是能够与世界对话的文学,这或许是西部文学创作及其研究得以跃上真正“高地”的大目光和大境界。(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