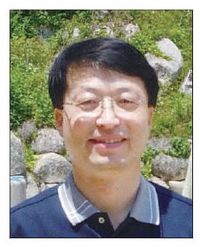
最早把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动向介绍到韩国的是梁白华。他翻译了日本人青木正儿的文章,并以“以胡适为中心的中国文学革命”为题在1920年11月的《开辟》上发表。之后,在1927年8月,柳基石翻译了鲁迅的《狂人日记》,以青园为笔名在《东光》上连载。1929年1月,梁白华在开辟社翻译出版了《中国短篇小说集》。自此,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及理论著作的翻译逐渐展开,特别是近年来,翻译出版活动表现得更为活跃。
形成了稳定的中国现代文学读者层
在梁白华、丁来东等人的大力倡导下,曾一度引起韩国社会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关注。但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和介绍工作开始受到重挫,特别是1937年7月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这项工作完全陷入崩溃状态。虽然在1945年光复后,曾出版了金光洲、李容圭译的《鲁迅小说选集》,但随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1950年韩国战争的爆发,两国的外交关系断绝,自此以后的数十年间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和翻译工作被迫中断, 留下了一段空白。
自1970年代起,这一状况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以1972年为起点,韩国中文系的数目迅速增加。虽然早在日本殖民地时代汉城大学就设立了中文系,但是直到光复前不过只有9名毕业生,光复后,每年也不过只有一到三名毕业生。到1972年,高丽大学、檀国大学、淑明大学先后设立中文系,之后逐年都有增加。到目前为止,韩国共有110多所大专院校开设了中文课程。
随着中文系的增加,由此培养了大批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专业人士及精通中韩文翻译的人才,而且,自然而然形成了一个稳定的中国现代文学读者层。与此相同的变化也体现在各种与中国现代文学相关的学位产生趋势上。到1980年为止的数十年间里,在韩国发表的与中国现代文学有关的硕士论文不足10篇,但进入1980年代以后,获得硕士学位的人数有了明显的增加。至于博士学位论文,1989年以来每年有数篇,尤其是1993年和1996年各有12篇。
中国现代文学的韩文翻译具体表现在以下门类的著作中。
理论著作(包括评论)的翻译
1980年以前,理论著作不过10本,之后,每年都有几本理论著作出版发行。最初,与作家介绍有关的书籍较多,如《当代中国大陆作家评介》(黄南翔,1985),《当代中国作家风貌》(彦火,1986)等。到1990年前后文学史类的译书相继出现,如《中国现代文学史教程》(朱德发,1989),《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黄修己,1991)等。
后来,理论著作的翻译发展方向则更趋于对不同文体的专门介绍,如《现代诗人及流派琐谈》(钱光培,1998),《中国当代散文审美建构》(李晓虹, 2000)等。值得注意的是黄修己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的出版。中国现代文学史是向中文系学生及一般大众介绍中国现代文学进展状况的最基本的著作。1991年翻译出版的黄修己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以其丰富的内容、完善的体系和文化现象优先的观点,堪称一部优秀的学术著作。到目前为止,历经四次再版,它对韩国中文学界的影响甚大。另外,一些学者翻译的日文版和英文版的著作尤其值得注意。如《鲁迅评传》(丸山?,1982),《中国现代文学史》(菊地三郎,1986),《中国文学この百年》(藤井省三,1995),《中国の荣光と悲惨:评传赵树理》(釜屋修,1999);以及Marxist Literary Thought in China(Paul G. Pickowicz,1991)。这些书的出版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观点,拓宽了信息渠道。但日文版、英文版书籍翻译的数目相对较少,还需作更多积极的努力。
小说的翻译
1970年代以前的译本约10本,1970年代的译本合计不过10本而已。但进入1980年代后,译本的数量逐年增加,到1980年代后期,平均每年都有10多本译本出版发行。特别是1992年中韩建交后,小说的翻译得到飞跃性发展,在1992年后的连续几年中每年都有30多本的译本出版发行。在 1997年韩国经济风波前后,小说的翻译工作暂时处于低潮,但后来又呈增长之势,小说翻译数量的演变,鲜明体现了中韩两国关系的改善对文学创作领域产生的深远影响。这里有几点颇值得注意:一是1989年中央日报社与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专家合作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全集》。这一全集共20本,其中包括16本小说集,散文集、诗集、剧本集和评论集各一本。这些作品贯穿中国现代文学的整个时期,堪称是各个体裁的代表作,译者大部分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各领域的专家,尤其值得注目的是容易被人忽视的台湾作品也被收录其中,这是以往不曾有过的飞跃发展,是中国现代文学各个领域的分散性研究的具体化。在可靠的译者与可信的出版社积极合作下,这一全集得以出版发行,必将给韩国普通读者以深远的影响。二是琼瑶小说的大量出版。自1980年代中后期起,每年都有两三部琼瑶的小说被译成韩文,但并未在韩国读者中引起强烈的共鸣。1992年,韩国的SBS电视台将琼瑶的小说《金盏花》改编成电视剧,这部电视剧深受韩国观众的喜爱,自此琼瑶的小说被大量译成韩文,仅1992年这一年间就有24个译本出版发行。迄今为止约有75个译本出版发行。我以为,琼瑶的全部小说几乎都翻译出版过,与琼瑶风格相似的大众作家朱秀娟、李碧华等人的小说也被大量译成韩文。三是长期以来在中国现代小说翻译过程中一直存在的问题,那就是鲁迅小说不断被重译出版的问题。其实收录在《呐喊》、《彷徨》、《故事新编》中的鲁迅的小说不过只有33篇,完全可将其编辑在一本书里出版发行。但目前为止出版的鲁迅小说却已达60本,这不能不令我们深思。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首先是因为鲁迅的作品具有极高的代表性,它是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开始的标志存在的。但从另一侧面看,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着大量的优秀作品,这种对特定作家的作品进行过分强调是否可取?鲁迅和琼瑶小说的译本多达135本,占小说翻译总量400本的 1/3。由此可见问题的严重性。还有,除大众文学外,中国港台的严肃文学作品很少被介绍到韩国。再就作品的时间而言,大多集中在1949年以前和1976 年之后,而1949年至1976年间的作品却相对少见。
散文的翻译
小说领域反映出的过于偏重某一作家的情况在散文领域也同样存在。不同之处在于:散文领域偏重的不是鲁迅等人的散文,而是林语堂的散文。在已出版的近 150本散文集中,林语堂的散文占了一半,并且在这中间,仅以“生活的艺术”命名的散文就有20本。1980年代以前翻译的中国散文绝大多数是林语堂的作品。尽管在1950年代到1990年代间,把林语堂的新作译成韩文的情况并不多,但这期间几乎每年都有几本林语堂的散文出版发行。林语堂的散文在韩国盛行的原因大概不仅在于其作品本身,还与他曾被推举为诺贝尔奖候选人以及后半生主要活动于海外,从事英文创作,具有非马克思主义倾向等因素密切相关。林语堂的散文集大多是以其英文版底稿为依据被翻成韩文的,因此可能会有人提出疑问,在韩国出版的林语堂的散文能否归入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翻译创作这一范畴。我认为,韩国的大部分读者一直认为林语堂是中国人,其作品是中国现代散文,况且以英文版形式出版的林语堂的作品中的大部分是其中文创作的英译本,因此对林语堂的散文理应归属中国现代文学范畴,这一点应该没有异议。总之,林语堂的作品对韩国读者影响很大,这一点可与鲁迅和琼瑶相提并论。与林语堂相比,鲁迅散文的韩译本相对不多,但仍有10多本,特别是李旭渊编译的《朝花夕拾》(鲁迅,1991)堪称是散文界的畅销书,深受读者喜爱。此外,载入韩国中学课本的《背影》的作者朱自清的散文集以及郭沫若的四本自传也都被译成韩文。鲁迅、朱自清、郁达夫等20世纪前期的优秀散文家的作品虽只有很少一部分被介绍到韩国,但毕竟还可见到。令人遗憾的是像杨朔、秦牧、刘白羽等20世纪中期以及贾平凹、王英琦等20世纪后期的散文名家的作品在韩国几乎找不到。让人略感安慰的是,1990年代中期以来散文集翻译的数量逐年增加,且并非集中于某一位散文家的作品,而是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例如,风靡于台湾和大陆的三毛、席慕蓉的作品已有几本被介绍到韩国,余秋雨的《文化苦旅》(2000)也在韩国出版。这不仅是出版社考虑商业利益的结果,同时也意味着这些与生活紧密联系的作品最易在读者中产生共鸣。
诗歌与剧本的翻译
与小说和散文相比,对中国现代诗和剧作的翻译显得大为不足。到目前为止,韩国出版的中国现代诗集只有25本左右。在此情况下,对中文现代诗的翻译仍有几点值得关注:一是许世旭翻译的《中国现代诗选》(1976)等几本诗集。许世旭不仅是一位优秀的学者,同时也是一位相当出色的诗人,无论是在选诗方面还是在翻译方面他都有其独到之处。二是艾青和北岛的诗有几本已被译成韩文出版,这也许与他们都曾被选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有关。三是近年来,顾城、傅天琳、舒婷等诗人的作品被译成了韩文。与诗歌相比,剧本的翻译显得更加惨淡,仅有《雷雨/茶馆》(曹禺/老舍,1989)等不足10部。剧本不仅是阅读对象,同时也是为演出服务的,因此,与其他文学体裁相比,剧本有不利之处。另外,此间在韩国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者中,攻读戏剧文学的人士很少,这也是剧本不能被大量介绍到韩国的原因之一。
如前面所述,到目前为止,与中国现代文学有关的韩文著述大致有理论书60本、小说400本、散文150 本、诗集25本、剧本10本,合计不足650本。如单纯从数字上看,这些似乎已经很多,但如果考虑到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翻译的历史,就不难发现,这个数字并不算多。况且,在这些译本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被重复翻译的,还有一些完全是为了迎合大众口味的低级的大众小说。认识到这些问题,我认为,对中国现代文学所做的翻译工作还是远远不够的。
还应注意的是,韩国除中央日报社编纂的全集外,其余大部分与中国现代文学有关的翻译都处于无系统的零散状态。这主要是由于出版社以及与中国现代文学有关的专家学者无计划的翻译造成的。出版与中国现代文学有关的书籍较多的出版社有弘益出版社(15本)、?友社(8本)、青年社(8本)、日月书阁(8本)、五?书(6本)、高丽苑(6本)、明文堂(6本)、惠园出版社(5本)、白山书堂(5本)。其中弘益出版社出版的主要是琼瑶的小说以及一些大众小说,其余的出版社出版的数量少,所以很难找到共同点。
重视翻译的作用
相对于学术论文和新闻纪事的翻译,文学作品的翻译具有更多的难点。这是因为一篇理想的文学作品应是一个完整的整体,它要求词语与词语之间甚至词语与符号之间互相呼应,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在这种情况下,把一篇文学作品作为一个完整的整体用历史与文化背景不同的另一种语言体系毫无损伤地翻译出来,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事实上,文学作品的翻译并非只涉及如何正确地把一种语言转化为另一种语言的问题。比这一点更重要的是如何正确地把握作品的内容,如何恰当地评价作品,以及怎样看待作者的创作观等问题。不同社会之间的互相接触不可避免地需要翻译工作,因此,尽管目前在翻译方面可能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但我们还不得不承认翻译的重要意义。我认为,在将中国现代文学译成韩文的过程中有几个难点应该注意:一是因缺乏对原文的理解造成的误译,二是漏译和添译,三是译文的不自然,四是原文的特殊性,五是名词的音译和意译,六是灵活运用的问题,七是直译和意译的关系,八是理论著作中文献名的统一。
今天,在影像媒体的影响下,人们对文学作品的兴趣逐渐减少。即使这样,跟其他领域相比,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翻译和研究像韩中两国的交流一样尚有很大的发展余地。再加上,参考前车之鉴,这方面的商业性成功也具有充分的可能性。因此,学术界也不能只把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翻译与研究交给市场,应该更有意识、更积极地倾注关心和努力。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一个更健全、更活跃的发展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