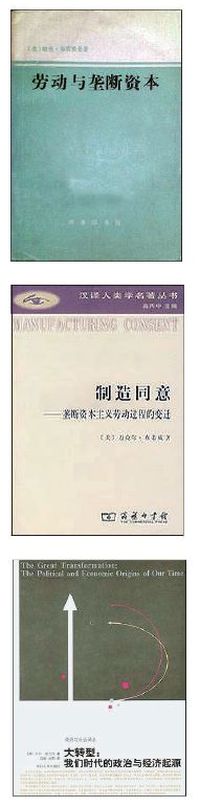
在马克思笔下,物化技术选择与革新所带来的技能替代是资本主义工厂内劳动政治过程的触发点。马克思技术理论为我们鲜活地展现了技能形成过程中的利益政治行为,也明示了一个不争的事实:劳动过程中的技能形成绝非只是一个技术更替的物理过程,更是一个充满冲突与斗争的政治过程。但时至今日,资本主义多样化发展的历史事实对马克思技术理论提出了新的挑战: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同样实行私有制的不同国家之间,相同技术传播的方式、速率以及结果为何会出现显著差异,而形成不同的技能体制呢?
马克思技术理论通过劳动政治这一中间变量将生产体制(或“工厂政体”)与技能形成勾连起来,但是在实际劳动过程中,与技能形成相关的制度安排绝非仅限于生产资料所有制,还包括企业治理的其他制度类型,如劳资关系制度、财政制度、培训制度、市场制度乃至国家体制,等等。而且其关涉的行动绝非仅限于劳资之间,它还存在于资方之间、技术工人与非技术工人之间、国家与企业之间,等等。
技能形成体制的两种类型
在韦伯理想类型的意义上,我们可以将资本主义国家的技能生产区分为两种形成体制:外部培训和内部培训。前者属于技能生产的外部替代,实现路径主要是通过自由劳动力市场,技能形成主体是职业技校,生产的技能类型多是可转移性的一般技能;后者属于技能的自我生产,主要通过在职或在岗学习和培训,技能形成主体是企业自身,由此生产的技能类型通常是不可转移性的特殊技能。梳理资本主义工业化历史,研究资本主义国家技能形成体制的专家们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即英美两个资本主义国家较青睐外部技能生产体制,而内部技能生产体制在德日两国一直都有很大的生长空间。这显然是马克思技术理论无法解释的。
霍尔(P.A. Hall) 和索斯基(David Soskice)将资本主义多样性技能形成体制的差异归因为资本主义经济治理制度类型的国家间差异。他们将资本主义国家划分为两种理念型:以英美为代表的自由市场经济国家和以德日为代表的协调性市场经济国家。他们认为经济治理制度与技能形成体制之间存在着制度匹配情况,但遗憾的是,他们对两种制度之间如何匹配的过程论述较少。
这里,马克思关于劳动政治与物化技术选择相关性的证明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灵感与路径:资本主义国家间不同经济治理制度导致了劳动政治类型的不同,进而形塑了各自技能生产体制的不同走向。我们知道,自由市场经济制度核心理念是主张撤销市场管制,最大限度地释放自由市场力量,保障企业与劳工自主权是经济行为治理的前提;协调性市场经济制度依赖联合网络限制企业间的恶性竞争,遵循关系性和不完全契约原则进行资源交换和企业治理。
已有经验证明,在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下,劳资间的劳动政治多表现为阶级对抗性的利益政治行为:一是企业与劳工都能够以自认为合适的方式自由选择技能获得的方式,企业间对技工的自由争夺行为顺理成章;技工则以自由流动来抵御劳动不安全的风险。二是工人尤其是技工间的联合与组织化拥有有利的政治和市场环境。企业和劳工的理性策略是尽量减少对彼此的依赖:资本家通过“去技术化”策略,引入半自动或者自动化机器以减少对技工的依赖;对于技工而言,则是以组织化方式去争夺自动化机器的专有使用权,同时多倾向于选择“可转移的通适性技能”以规避劳动不安全的风险。这样,外部技能生产体制在劳资双方合力推动下水到渠成。
相反,协调性市场经济制度却为社会不同阶级“搭建了一个调和利益的现代模式”,劳资之间的跨阶级联合成为主要的劳动政治类型,德国著名的“社会伙伴制”即是最好注解。在这种“社会管制资本主义”制度下,企业通过行会组织、同业协会、卡特尔等非市场性治理机制限制自杀式的恶性竞争行为,监督和惩罚行业中的“挖墙角”等资源争夺行为,而且劳动管理的“反利润”原则为劳工的劳动安全提供了后盾。换言之,内部技能生产所面临的“可信承诺”与“集体行动困境”等问题通过跨阶级联合的劳动政治类型得到了有效克服。
对中国的启示
在全球化生产链异常发达的今天,技能生产体制被公认为是一国形成“比较制度优势”的基石性制度安排。众所周知,装备制造业是组成国家竞争力的支柱性产业,它的创新属于一种累积性创新模式,与注重时效的外部技能生产体制不同,注重长期积累的内部技能生产体制则更有利于累积性创新模式的发展。面对中国国有制造企业中内部技能形成方式(如师徒制)日益衰微的境况,重新回到马克思、讨论劳动政治与技能形成的相关性,对于思考国有企业改制、社会保护性劳动政策的制定以及装备制造产业创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