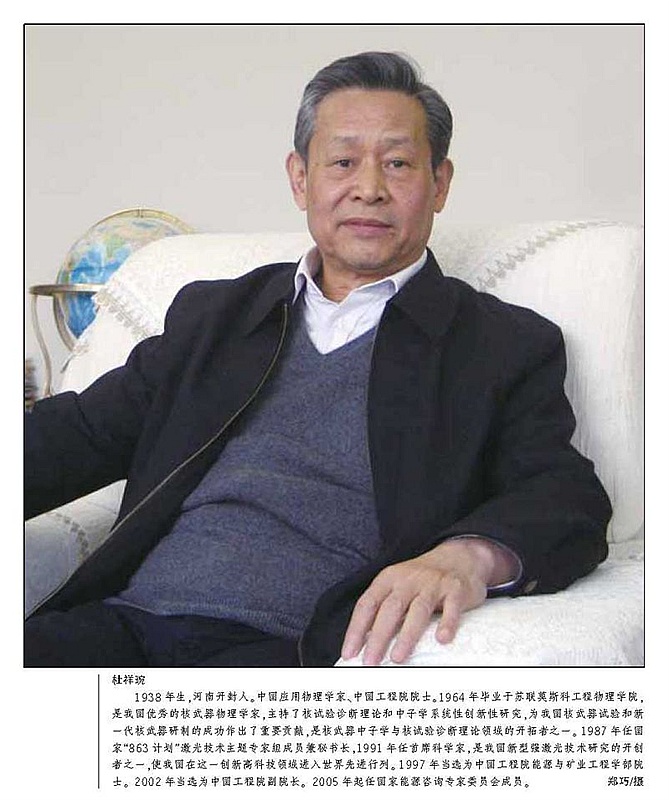
杜祥琬 1938年生,河南开封人。中国应用物理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1964年毕业于苏联莫斯科工程物理学院,是我国优秀的核武器物理学家,主持了核试验诊断理论和中子学系统性创新性研究,为我国核武器试验和新一代核武器研制的成功作出了重要贡献,是核武器中子学与核试验诊断理论领域的开拓者之一。1987 年任国家“863计划”激光技术主题专家组成员兼秘书长,1991年任首席科学家,是我国新型强激光技术研究的开创者之一,使我国在这一创新高科技领域进入世界先进行列。1997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能源与矿业工程学部院士。2002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副院长。2005年起任国家能源咨询专家委员会成员。
第一次见到杜祥琬院士,是在“两弹一星历史研究高层论坛”上,身着简朴便装的他在讲台呼吁,“科技界要像防控SARS和‘甲流’一样,坚决抵制各种不正之风,回归科学精神的圣洁”,字字句句掷地有声。
不久后,在中国工程院的办公室里,杜院士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就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改善学术评价机制和培养创新型人才等社会广泛关注的问题发表了看法。
1 严谨、创新、献身精神需代代相传
记者:您在“两弹一星历史研究高层论坛”上提到,弹也好,星也好,造假是造不出来的。您对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有哪些具体建议?
杜祥琬:我一直很关注这个方面,因为科学界出的事情比较多,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在2009年9月7日举办的第十一届中国科协年会“科学道德国际论坛”上,我作了题为“科技繁荣和科技道德”的演讲,归纳了13类违反学术道德的行为,包括论文著作造假、抄袭、剽窃,靠拉关系、靠“忽悠”来争项目、争经费等。针对这些问题,我提出了16条建议,分为教育、制度、监督、法制四方面。
记者:您觉得这16条建议具体要由谁来执行呢?
杜祥琬:中国科协主席韩启德也问我,这个药方开出来,谁当大夫。我首先想到一句话,从来没有救世主,只有自己救自己。所以首先要自立,科技工作者、学术共同体要自己治自己的病。同时,还需要各个单位、协会以及政府参与。其中制度、监督、法制都有赖于政府主导。
这个药方是中药还是西药?我觉得要中西结合,因为西药见效快,中药可以治本。科技道德既是一个紧迫的问题,又是一个长远的建设。
记者:您觉得这“16服药”中哪个最重要?
杜祥琬: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教育,因为自律是关键、是核心。自律是一种素养,这种素养植根于教育。而最深刻的是制度建设,因为制度可能涉及多方利益,是根本性的问题。
中国科协有个调查报告提到,60%以上的人认为现在科学道德下滑,而且有50%以上的人认为现在年轻群体的状况最不好。我个人倒宁可希望这些数据是错误的,但既然这么多人持这种观点,我觉得是有原因的。
记者:您曾提到,科学精神、科学道德和良好的学风是科技繁荣的灵魂支撑。有哪些学者的科学精神最令您钦佩?
杜祥琬:我经常给学生们讲老一辈科学家的故事,倒不是具体研究的故事,而是他们所表现出来的科学精神。
比如王淦昌先生,他是实验物理学家,原子弹突破的带头人。抗日战争期间他在西南联大教书时,从理论上提出了中微子测量的新方法。但因为当时中国被日本侵略,没条件做试验,《物理评论》发表他的文章后,美国人拿去做了实验。1960年,王淦昌前往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工作,他领导的研究小组发现了反西格马负超子。
1961年,当国家要他回国搞原子弹的研发时,不善言辞的他只说了一句“我愿以身许国”,从此王淦昌就从大众视野中消失了。他本是国际知名科学家,从1961年到1979年18年间隐姓埋名地干这件事,连家人也不知情。他在杜布纳研究所时,有一张胶片显示了一种“新路径”。他的国外同事想对外宣布发现了新粒子,但他表示没有理解这种现象前不能仓促宣布。后来经过分析,这是一种介子的电荷交换反应,而不是新粒子。大家都知道他发现了反西格马负超子,但很少人知道这件事,因为这不是一项成就,但这件事恰恰证明了他严谨的态度。
刚去世的钱学森老先生,在最后一两次谈话中提到和自己一起在加利福尼亚求学、一起回国的郭永怀。钱老是搞导弹的,郭老是搞核武的。在离开美国时,郭老知道资料过不了海关,不得不烧了自己的手稿。他的夫人觉得很惋惜,但郭老指指自己的脑袋,说都在脑子里呢。
老一辈科学家身上严谨、创新和献身精神,让人非常钦佩。他们也有很深厚的功底,我有幸在他们身边工作,他们留给我们的这些精神,都是值得年轻一代学习和传承的。
2 充分发挥学术共同体作用
记者: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很多学者质疑现行 “量化”式的学术评价和管理机制,很多人认为用它来评价人文社科研究不适合,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科研的浮躁之风。在评价体系上自然科学和人文社科是不是应该有所区别?
杜祥琬:不仅自然科学领域和人文社科领域的评价体系应该有差别,而且自然科学领域中的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的评价标准也应该有所区别。如果只有一个标尺,那就不大对了。比如说SCI,其实并不是与国际接轨的做法,国外也不单纯以SCI来判断学术成就。
当然,SCI也不是完全没有用处,可以用它作为基础科学的评价参数。但是应用科学是个复杂工程,是多种技术的集成,衡量标准应该是能否很好的应用,不能拿SCI作尺子。比如研制原子弹、氢弹,就不允许发表文章,即使研制成功了也不能发表文章。
核武器原理突破后,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但排名第一的彭恒武先生却不愿领这个奖,他说这是集体的成果,并以一副对联作解释:“集体、集体、集集体;日新、日新、日日新”。换做现在有些人,肯定会抢着去领。争排名的人太多,甚至为得奖去炮制成果。这样的研究,用SCI评价,是不合适的。但搞基础研究,论文还是非常重要的。不同类型的研究,应当有不同的评价标准。
人文社会科学更应该有自己的评价体系。从根本上说,科学就是要追求真理,造福人类。你要看新认识、新知识增加了多少,在造福人类方面又贡献了多少。应该用对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所作出的贡献作为衡量标准,具体的评价标准应该有所不同。
记者:那具体该如何订立标准呢?像高校人文社科的评价机制已经逐步从重量向重质转变,但是这项工作做起来是不是比较困难?
杜祥琬:确实,这个工作比较复杂,但是过于简单化也不行,所以我提倡学术界要一起探讨,创造有利于创新,也比较公正的学术评价体系。比如,发挥科学共同体,或者说发挥同行们比较“超脱”的评价。不单纯以奖项和文章数量来评价,让集体来评价研究价值。但这个集体评价需要一个组织和一种机制,我觉得可以想办法来解决。
记者:您觉得集体评价在中国可以实现吗?
杜祥琬:国际上的客观评价都是这么来的。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就是靠一个集体来评价的。由一个比较权威的科学家的集体,评价或者挑选出一些最优秀的,我觉得这就够了。中国现在的奖项评得有些乱,甚至有些奖项内容并不实在,奖项的排名背后也有各种各样的因素。比如把掌权的人排在前头,有不少这样的例子,这些都不能反映科技工作者真正的状态。
记者:现在有种说法:有些奖评出来,获奖者中有行政职务的占了百分之七八十。
杜祥琬:是的。有行政职务的,或者出经费的人在获奖者中占的比例很高。前不久评选了中国100位优秀教师,90来位都是校长,真正在第一线教书的只有10位。这就是现在的问题,行政化、官本位严重。权力的因素在评价中占的比重太大,学术环境不够纯净。
[page] 记者:基层的学术共同体操作起来会不会比较困难?
杜祥琬:学校本来就有教授共同体,而不是让校长、书记说了算,要各司其职。如学校如何教学、如何育人、如何做研究等问题,应该要让教授说了算。实际上现在并不缺乏这种组织,而是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当然,解决这个问题确实不容易,涉及一个国家的体制改革。
记者:改变这种状况是不是很难?比如,有的高校想转向“教授治学”,但在转变过程中行政权力的干涉程度仍旧很高。
杜祥琬:大家都很关注这个问题,像南方科技大学在做试验。但究竟能不能做好,也要慢慢看,这也是教育改革、科技改革的一部分。学习科学发展观一定要落实到这些具体问题上,用科学发展观来引领科研实践、教育实践,光喊口号是不行的。
3 真理没有国界
记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学术文章被“CI”期刊刊载,就代表具有国际水平。现在,这种“CI崇拜症”已经遭到越来越多专家的质疑。您对中国学术界这种“国际化”的追求有什么看法?
杜祥琬:我觉得在全球化时代,不能关起门来评价自己,还是要有国际视野。包括让国际科技界来参与我们的评价,但这与本土化并不矛盾。如果没有本国专家的承认,国际上的认可又有什么用?而且,国际上会认可吗?
如果属于新发现类的,就是说对客观世界有新的认识,国内和国际的学术评价应该是相同的。比如双螺旋结构DNA的发现,就无所谓国际还是本土了,因为科学本来就是无国界的,评价是统一的。比如我们曾经人工合成牛胰岛素,国内国际评价都很高,都很一致的,这说明真理是没有国界的。
至于如何改造世界的问题,针对社会、国家发展的需求提出的问题,比如说建一座大桥、一座大坝。能否做好,国内、国际都会有一个认可的标准。首先中国科技工作者要有一个公正的评价,我想国际上的评价也会公正的,不必在名词上争论这个问题。社会科学领域有些问题可能更复杂,因为涉及政治,而政治评价标准不同。
社会科学的评价标准,我觉得主要看是否有利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说得窄一点,就是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说得广一点,就是人类和世界的可持续发展。这也是共同的利益。但这里面掺杂了复杂的政治因素,与国家利益有关。我们“和谐世界”的提法很好,强调要有利于中国人民,也要有利于世界人民。当然,由于政治因素的影响,国际上有些评价的确有失公正客观,包括诺贝尔和平奖。
4 品格成就科学家
记者:去年10月31日,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在京去世,钱老生前曾多次向温家宝总理提出人才培养问题,对中国缺乏杰出人才深表担忧。您对人才培养有哪些建议?
杜祥琬:我想钱老提这个问题,是因为他感觉到现在国家经济发展了,学校也越来越大,但是却出不了大家。
要培养创新型人才,首先要厘清教育理念。现在的教育理念不够清晰,受过诸如“政治挂帅”、“金钱挂帅”等许多因素的干扰。学校如果仅仅以挣钱为目的,会对学生产生不利影响。教育的使命是育人、治学。政治化、企业化都不合适。最重要的是要教会学生如何做人。不管学生将来做什么,做一个正直的人是首要条件,如果这一点都做不到,那么什么都不可能做好。
创新型人才的培养,需要从孩子抓起,使他们逐步树立一个好的价值观。现在社会上价值观呈现出多元化,我们要正视这件事,但是还要引导、追求、鼓励高尚的价值观,要强调为社会、为国家作贡献,不能狭隘地损人利己。爱因斯坦曾说,大多数人以为是才智成就了科学家,他们错了,是品格。好的品格能为理想提供动力。
培养创新型人才,还应该鼓励学生生动、活泼的个性,去思考各种各样的问题,不要老以是否听话为标准去教育学生,学生讲新观点好像就是离经叛道一样。一定要鼓励各种各样的想法,想别人没想的问题、回答别人回答不了的问题。对学生的教育要从小培养他们的兴趣,鼓励大家思考,鼓励发明创造。如果不是这样,就培养不出创新型人才。
此外,我觉得培养人才还需要鼓励交流。有了观点就要交流,这很重要。比如钱老经常在开会时讲他的新观点。别人说,你一讲大家不是都知道了吗?钱老说,“那怕什么,多多交流,我马上又能有新的想法,这多好呀,让别人也提高,我也提高。”现在有种情况,有的人有了新的想法总爱保密,不交流。这样水不涨,船不高,都进步不了。像我去过的一些国外研究机构,每周五下午大家都会聚在一起聊天,交换新观点,让思想碰撞出火花。如果只是循规蹈矩地学习,不交流,那就很难创新。
我希望现在的学生们都拥有两个动力,一个动力是好奇心,第二动力就是服务社会的理想。要让这两个动力像两个轮子一样驱动自己的人生。
记者:“两弹一星”的元勋中很多人都有国外留学的经历,留学经历对一个人的学术研究、创新精神也有很大影响。
杜祥琬:我曾在欧美同学会上讲过一个观点,海归不等于杰出,杰不杰出要靠成果说话。当然,海归有个好处,国外工作条件比较好,周围有一批高素质人才,有助于青年的快速成长。现在也确实有一批归国人才做得很不错。
改革开放就有这个好处,利用国际大舞台,利用国外的资源和环境来培养人才。但是,不能偏执地说在中国的土地上就出不了人才。有事实为例,袁隆平就不是国外培养出来的。对氢弹试验成功作出重大贡献的于敏先生,是北大的毕业生,土生土长的人才。中国的土地上是可以成长出人才的。王淦昌在莫斯科发现了反西格马负超子,但他的这一成就是在西南联大时想出来的。西南联大治学育人的校风很好。校舍虽然很简陋,但有很好的学风,出了一大批人才,李政道也是在那求学后才出去的。
我们鼓励人才走出去,国家也很重视从海外引进人才。但是我觉得不应该忽视国内人才,包括早期归国的人。现在国家对留学归国人员有很多优惠政策,但对比他们更早一批的留学归国的人,却没有鼓励,政策上其实有失偏颇。我们是要鼓励大家在国际大舞台展示自己。国内学者也要参与国际上的学术研讨和比较,袁隆平之所以获得广泛好评,是因为他对世界也作出了贡献。
5 自然科学研究带有初级阶段的特征
记者:我国的经济成就已经获得了国际认可,我国自然科学的成就在国际上大概是处于什么地位?
杜祥琬:从经济上看,中国取得了较大成就,目前是世界上第三大经济体,很快就要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但也面临一个严峻情况,我国的人均GDP大概是瑞典的1/15,挪威的1/30,在世界上的排名大约是106名。所以,只能说我们进步很大,但仍是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
十几亿人口的国家如何保持可持续发展,是我们目前关注的首要问题。金融危机以后,国际上纷纷赞扬中国模式如何成功,但我们要保持头脑冷静。我们有了一些经验,但还没有一个成熟的中国模式,只能说,中国人在力求成功。从党中央一直强调的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中也可以看出,中国有13亿人,走得好是非常不容易的事。
我国的自然科学研究总体上是在进步的,但就像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样,自然科学研究也带有明显初级阶段的特征,即规模大、数量多,但核心竞争力差、原始创新少,这些问题必须正视。我们不是没有创新,也有很好的中青年学者在成长。但总的来说原始创新少,其中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可能不少,这些问题在初级阶段还是要重视的。我们在许多方面做得不错,这是实际情况。但有多少原创性的东西是中国提出来的呢?这要看大家能不能潜下心来去解决未决的问题,而不是急功近利地发表文章和评奖等。
中国自然科学研究在国际学术上的名次进步确实很大。中国科技论文数量排世界第二。科技论文数量增长很快,申请的专利成果也增加得很快,这是进步。但是质量如何,要自己问问自己。我们的科技论文、专利的数量,跟它发挥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不相称,生产力的转化还是很不够的。
记者:像“贝尔实验室”在全世界非常有名,中国现在有顶尖的实验室吗?
杜祥琬:应当说,我们完善了不少实验室,有些设备也相当不错。我们也研制出了一些功能比较优异的材料,在一些点上取得了进步。但总体上来讲,缺乏国际一流的大学和国际一流的实验室。大家都在追求做世界一流大学,但没人敢说我就是世界一流大学,我们的大学和世界一流大学相比还是有差距。冷静地看到差距,大概没有坏处。
很多事情,如“两弹一星”,都是中国人在国外不给帮助的情况下创造出来的,“载人航天”事业也是很有成就的,虽然晚了几十年,但毕竟是在人家不帮忙的情况下创造出来的。我们在努力向前,这是值得承认的,但不能说我们领先了,现在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的成果还不多。
6 加强人文和自然科学的交叉研究
记者:您对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还有哪些建议?
杜祥琬:我一直想强调,要加强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交叉研究,共同推进国家的科学发展。现在很多问题都涉及了交叉研究,像“两弹一星”历史研究会就是一个具体例子。研制原子弹、氢弹本身是自然科学界的事,但既涉及自然科学的发展,又涉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该如何去继承和发扬“两弹一星”精神,类似这种问题都不是自然科学可以容纳的,需要与人文社会科学进行交叉研究。
一个国家的科学发展,既涉及自然科学,又涉及人文社会科学。比如核军备控制,这个问题一方面包含如何销毁核弹头,如何进行核查等技术性的问题,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另一方面又涉及政治和外交斗争,属于人文社会科学范畴。应对世界金融危机和气候变化等问题,也涉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交叉。所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三院应加强交流,展开交叉研究。